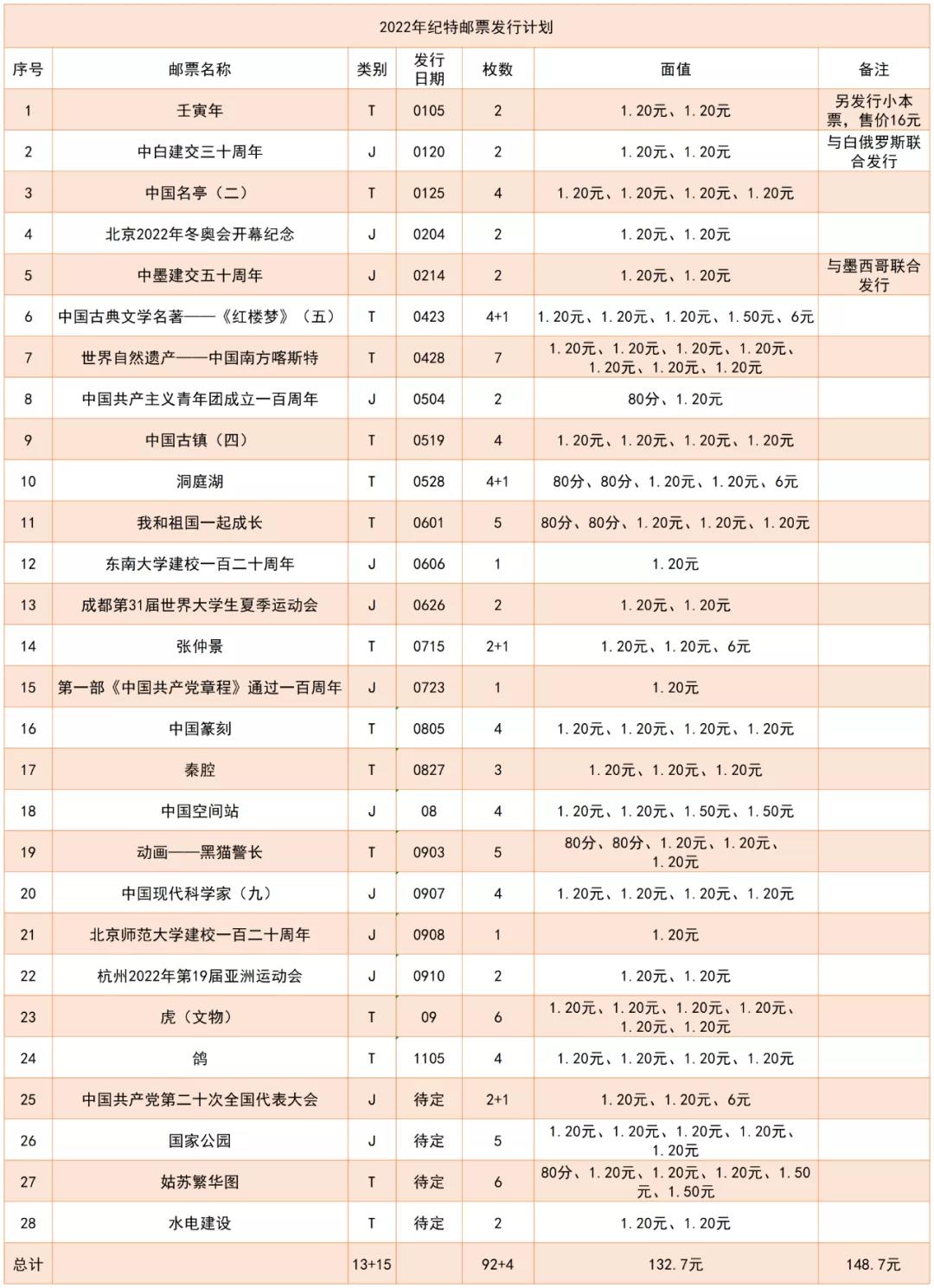内容提要
余华的《文城》与《兄弟》一样,上下两部文本之间差别极大,实际上《文城》上部的“混乱”是在为下部“造势”。上部是以林祥福为焦点的“梦幻叙事”,夹杂着类似鲁迅创造的阿Q式低智视角带来的混乱,有些“反英雄”“反传奇”甚至“反叙事”,故事碎片化为一个拼接式的后现代文本。而下部《文城补》却画风突变,转而变为以小美为焦点的“蝶梦庄周”式“人间叙事”,带着川端康成式的哀伤,其间上部的不和谐因素全部消失,叙事极其稳定流畅,达到近乎行云流水般的情境。小说叙事所呈现的“哀伤”其实已超越了川端康成,个人的苦难和生死之下,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命力的写照与生存伦理的史诗性表达。《文城》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余华创作中的第四次重大转折,其叙事转型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无疑都有重要意义。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关键词 余华;反英雄;双重叙事;川端康成的哀伤;生命力
余华40年的创作生涯历经数次转折,从后现代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一举成名,到现实主义式表达的《活着》的享誉世界,再到消费主义式书写的《兄弟》的巨大争议,每次新作出版都激起热烈的讨论,几乎每部作品又都在商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余华每部新作似乎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否定与“进化”。2021年余华新作《文城》出版,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争论热点之一即上下两部不论文风还是主题都差别巨大。《文城》上半部的阅读体验相当糟糕,以致让人以为《文城》可能是余华在《第七天》之后更糟的一部失败之作;但是,后半部分《文城补》却能让人凝神静气地一气读完,似乎抵达了另一个世界。《文城》前半部的“乱”似是为了托出后半部的惊艳,即《文城》较为成功的叙事部分实际上是后面的《文城补》。
《文城》腰封上印有:“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字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这种格言式的话语类似《读者》式的抒怀随笔,其预期接受者则指向一般大众,看得出余华的“理想读者”[1]群或消费对象就是《活着》培养起来的忠实读者甚至是文学粉丝群。看来余华的定位是青年化的,这种青年化定位往往损害作品的深度。但是一切却又似乎颇为出人意料,余华的《文城》不但赢得了大量的普通读者(年销量百万册[2]),而且还赢得了“专业读者”[3]的赞许甚至敬佩。
一 “反英雄”下的“混乱”:“梦蝶”式碎片叙事
从叙事策略上看,《文城》的叙事表层充满着“《活着》风味”,特别是那种温情叙事式的缓慢叙述,主人公林祥福的命名也极像《活着》中的徐福贵,皆为“姓氏+财富+吉祥”式命名,内蕴着中国乡村的乡愿与生机。《文城》并未采用《活着》的第一叙述人和第二叙述人同时存在的双时空交叉叙事,只有一个说书人似的隐藏叙述人几乎不作叙事干涉,整体上和古典式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类似,时间线条也是古典式的单线顺序叙事,或者是经典的矢量性现实主义式叙事。从叙事策略上看,叙述人似乎不断留白,很多因果关系没有交待,以致小说叙事中主人公的生活时常如幻梦;但这种梦幻感又无诗意诗性,而是有些类似鲁迅《阿Q正传》中以阿Q为视点的段落,给人很强的由智商低下带来的无知感。这样的“述而不作”似乎起不到中国山水画的留白效果,倒像一个智商偏低的人在人群中飘忽不定,周围是嘲讽的眼睛。从文本中来看,嘲讽不是来自众人,恰恰来自隐含作者投射的那个叙述人,如同鲁迅的叙述人对阿Q的凝视——同样都不给“深渊”回报以“凝视”的机会。
可以说《文城》的叙事是以林祥福为焦点建构的,小说叙述很多现象学意义的上、低层次的“还原”式感知也来自于他。由此小说中那种低智的梦幻感就可以解释了。《文城》上部类似“庄周梦蝶”,因为《文城》一开始,主人公林祥福就处在寻找妻子小美的“寻梦”之中。这样来审视《文城》叙事上的飘忽不定,倒多了不少合理的色彩。
但“梦蝶”之境事实上却是一片混乱。那个林祥福之“蝶”似乎经常浑浑噩噩,语言上都经常出乎意料。如在余华之前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修辞上的“小伎俩”也继续出现在《文城》中,这种伎俩意味着故作幽默,像《活着》中老年福贵讲完苦难史之后对“我”随口就扯上几句乡野荤话,似乎一个60岁老人还经常和30岁的年轻人一样“不正经”。我们看《文城》中的一个例子:林祥福的女儿林百家与陈家儿子陈耀武相恋,但由于林百家已许于首富顾家,因此被父亲故意送到远离家乡的上海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的“哭室”,林百家“百感交集,伤心蜂拥而来”[4],这主要是因为她想到了陈耀武。从心理学层面来看,现代科技使人类情感的精确化、数字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据相关研究显示,自然产生的人类快感(以多巴胺的分泌量为准)最高指数指向爱情;另一方面,人类痛苦最高指数指向失恋或恋人离世,所以失恋摧毁了很多人真不能怪人类太脆弱。况且几乎所有人的一生都有可能经历一次甚至几次相恋和失恋。所以,可以想象初尝爱情幸福感的林百家失恋后有多痛苦。但余华在此时却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修辞:“伤心蜂拥而来”。按说,“蜂拥而来”作为汉语常用的四字词组,其修辞效果多指一些实体数量极大且快速地、主动地移来,如街上的人、天上的云、地上的蚂蚁都适用此修辞,“自主性”很关键,行动主体一定要有自主行动能力才能“蜂拥而来”;而此处的“伤心”作为主观情感,是被动且抽象之物,不可能会主动地“蜂拥而来”,稍有点文学修养的读者读之都会有怪异感。
从正面来说,余华意在达到俄国形式主义所创的“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将其解释为“使事物摆脱知觉的机械性”[5]的效果,即打破固化或僵化的一般性语言,以陌生、怪异的组合或用法达到震惊的接受效果,从而完成“诗感”或“诗意”的创造。从中国的语法研究来看,郭绍虞认为这种现象是汉语灵活性的表现,是修辞突破语法规范[6],或可说是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的中国表述方式。不可否认,余华此处的“陌生化”效果相当成功,这也是始终贯穿余华创作的独特修辞特色之一,如《第七天》中“我”的出生是从母亲的子宫里“脱颖而出”、《兄弟》中兄弟两人在宋凡平的坟前眼泪“脱颖而出”,皆是以“错位修辞”打破语法规范,形成巧妙而奇特的隐喻或跨喻。但总体上来看,“蜂拥而来”在此处产生的修辞效果颇值得商榷,和两个“脱颖而出”一样,似乎都与语境不合,这种用法有叙述上的自我摧毁之嫌。在这个人类痛苦指数最高的失恋场景中,伤心“蜂拥而来”的情感指向似乎并不是正面或褒义,本来它是对人物行为和心理的全知式描述,但如此怪异的“陌生化”组合却将之变成了隐含作者的叙事干涉,隐蔽地加入了权威叙述人自己的情感,带有相当明显的幸灾乐祸之感,破坏了叙述人极力渲染的痛苦语境。这或者又可以看成60岁的余华的活力的表现:余华到老都维持着青年式的顽皮,这其实也是一种激情,一种叙事上的强大动力。
不过,《文城》上部中这样的错位修辞并不多,远不及之前的《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作品里面的多,我们在阅读上部中大部分文本内容的时候感觉到的是叙事上的混乱,以及傻子式的低智商视角看世界,很多场景的叙事非常像鲁迅《阿Q正传》中以阿Q的视点叙述时的呈现愚昧无知感。特别是林祥福怀抱尚是小婴孩儿的女儿、身背一个巨大的包袱去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文城,飓风卷走女儿却又失而复得,包括让刚满月的女儿吃百家奶,都非常让人疑惑,到底是林祥福出了问题还是隐含作者余华出了问题?
《文城》上部在叙事上经常呈现出粗糙而随意之感,特别是情节和场景的设置,很多地方像农村戏班唱大戏般随意而且漏洞百出。小说以林祥福怀抱刚满月的女儿寻找小美为开端,父女初到溪镇时,从陈永良的视点描写其女儿:“她的嘴唇紧紧咬合在一起”。本来是客观描述,但后来又加了一句“似乎只有这样使劲,她才能和父亲在一起”[7],这句话实际上是陈永良的心理活动,从修辞效果来说其实是自我摧毁式的叙事,这种突然转入人物心理的描述,并未强化林祥福的悲惨或悲壮之境,反而像中学生作文一样因为叙述不恰当而显得有些拙劣,不如去掉后面那句,只采用“嘴唇紧紧咬合在一起”就足以说明刚满月的女婴的悲惨状态,多了后面那句反而暴露出叙述上的不当与生硬感。
再有,《文城》的叙事节奏极快,经常出现不合理地跳跃性的叙事推进。叙事速度与叙事时间直接相关。叙事时间一般用页码来表达,“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长短的比较,前者用秒、分钟、小时、天、月和年来衡量,后者用文本长度(行和页)来测量”[8]。《文城》的文本叙事时间才至第90页,林祥福的女儿12岁时就和首富顾益民的大儿子定亲,之后,文城和小美都消失了,叙事时间此时才达到全书的%。庄周之蝶似乎从此倒成了没头苍蝇,整个叙事显得更加混乱。如叙述人大写两家订亲时首富的聘礼:五千银两、绸缎、金戒指、手镯、项链等,然后林祥福这边陪嫁良田500亩和各类日用器具及四季衣裳,又极力渲染宾客之多、菜肴之丰盛,试图营造出极尽奢华的首富和二富联姻的宏大场景。但整个场景都似是而非,叙述人时常给人一种感觉:他没有能力来把握这些场景,他展示的所有东西都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两个巧舌如簧的骗子,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其实你眼前什么都没有。
从情节设置上来看《文城》,问题就变得更加清楚。《文城》的叙事线索非常简单,中心应该是林祥福寻找小美,借助普罗普的“功能”理论和托多罗夫的“平衡结构”理论,能较清楚地分析出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结构,其情节的功能单位如下:
1林祥福相亲失败(缺失/失衡状态)
2美丽的小美出现(出现/平衡可能一)
3小美嫁给林祥福(结婚/平衡达成)
4小美第一次消失(离家/再次失衡)。
5小美带着身孕回来(回归/第二次平衡)
6小美第二次消失(离家/第三次失衡)
7林寻找文城(寻找/平衡的可能二)
8林认定溪镇是文城(抵达/平衡可能三)
9遇上陈永良和顾益民,受助养女儿(协同/帮助者功能)
10女儿被土匪绑架(加害/旁支失衡)
11军阀导致赎票失败(意外/旁支失衡)
12顾益民被土匪绑架(加害/帮助者失衡)
13林祥福主动去交赎金,身死(主人公死亡/平衡仍未恢复)
14陈永良智杀土匪头目张一斧(战胜/英雄已死,旁支平衡失去意义)
由于当代小说远比普罗普分析的民间文学样本复杂,特别是经历了后现代洗礼的小说更显复杂,故仅能在似是而非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但这已足够分析出《文城》的情节结构。“功能”指“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9],它类似戏曲中模式化脸谱化人物的固化作用,它会在同一作家的作品里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被不断重复,构成一个个的情节。托多罗夫的平衡理论则分析情节结构是如何完成的,即“最小的完整情节由一种平衡到另一种平衡的过渡组成”[10],可以用之分析情节的完成状态。《文城》的情节不但很常见,而且还非常简单,“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其实也都同样简单。从析出的14个主要功能来看,《文城》上部叙事线索混乱。前9个功能是主人公和小美之间不断地平衡和失衡,叙述人却没有说明两人行为的意义,小美为什么消失及林祥福为什么破釜沉舟般地去追寻?不仅都未给出理由,而且情节推进快速到不合情理。第10—14项这5个功能是土匪意外出现,类似英雄遇到意外变故,但这与前9个功能几乎没有关系,而且到主人公死去都没再提过“寻找小美”这一叙事主功能,作为具有重要象征功能的“文城”也再未出现。小说名为《文城》,小美是文城的象征,但文城和小美在小说大半篇幅中消失了,人们都唱大戏似地打土匪去了,隐含作者甚至草草安排了主人公的死亡,余华似乎把林祥福作为主要人物的基本任务都忘了。
如果按照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11],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些“行动元”的行动都不完整,和前面的那些普罗普意义上的角色“功能”多数得不到正常实现一样,本该完成某个功能,如“离家”“寻找”“缺失”“协同”“加害”“战胜”等,却都有始无终,最后的“目标达成”更是不可能实现,因为最关键的行动元“主体”就行为混乱,故事进行到一半时英雄的目标就莫名其妙地由“寻找”转换成了“打土匪”。小说人物的出现和消失也多数不太符合叙事规则。比如打土匪“旁支”中,陈耀武被绑架时,作为其父陈永良的异姓兄弟兼主人公的林祥福在做什么?其实,在这旁支中如果林祥福仍然不忘小美和文城,那么“主体”的功能还是有效的。但是,“主体”却消失了。从人物的“主体性”上看,整个《文城》前半部分,没一个立体的人物,全部面目模糊,毫无“主体”感,包括林祥福这个人物的刻画都一直是漫画化的风格,性格上稀里糊涂,女儿林百家被送往上海的情况也没什么交待,和林百家订亲的顾同年被人贩子卖给外国劳工船,后续也没有作交待。其他的人物也全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般,行为都存在着诸多不明和可疑之处。另外还有诸多并不必要出现的野合和嫖娼等的场景描写,特别是北洋军阀排数千米长队嫖妓的“壮观”场景,给人感觉是《兄弟》中富豪李光头举办的“处女选美”大赛又重现了。这些可以说都指向隐含作者所作小说叙事建构的失败。
总之,《文城》上部很多故事,叙述人似乎都讲不下去,因为缺乏兴趣或者激情甚至形不成有真实感的细节,以致给接受者随意编造之感。林祥福化身庄周之蝶后,叙述人附身于林祥福采取的阿Q式的“弱智视角”实际也在不断地自我摧毁,鲁迅使用“弱智视角”天才地塑造出了阿Q这个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需要被启蒙的“国民性”的代表,但《文城》的叙事效果却相反,主人公林祥福始终是个正面人物,并不是余华想启蒙的对象,但小说中却频频地以混乱的叙事将其貌似弱智化,不禁让人叹息:60岁的余华到底想做什么?
而当和《文城补》作比,可知余华很有可能是刻意而为,在这点上余华貌似又重演了历史——2006年《兄弟》上下两部差别极大。但2021年的《文城》上下部差别更大。《文城》上部的随意和粗糙,极似“后现代时期的余华”又回来了,特别是主人公林祥福的奇怪的死亡,几乎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死亡,与英雄没什么关系,就是一个木讷笨拙的平民无谓地死于土匪之手,让人感觉余华1989年的后现代式“反传奇”“反英雄”故事——《鲜血梅花》式叙事又重现了:一切都在别人掌控之下,侠客不论多强多厉害其命运却都牢牢掌控在别人手中,而且其人生显得毫无意义,名扬天下毫无意义,复仇也毫无意义。林祥福为了爱情而死,却如此平淡和庸常,似乎又是余华1988年的反才子佳人故事《古典爱情》的叙事再现:一切都是幻象,再坚贞的爱情都抵不过一场天灾人祸,甚至相爱双方的执着和执念都随时会摧毁那哪怕都跨越了人鬼界限的爱情。再者,也有可能余华在面对《文城》前半部分的写作时,实在无法投入真情感,以致叙事上力不从心。因为,他最关心的东西其实就在、且只在《文城补》里。所以余华在《文城》上部很有可能是设置了一个颇为“后现代”叙事的布局,反而是把小说的关键部分放在序言或后记里。
也就是说,《文城》这部小说实际上并不差,但这不差,全是因为有《文城补》。或者可以说《文城补》堪称余华一生创作中所发生的第四次重大转折[12],这次转折的意义甚至不逊于当年的《活着》。此时余华创作不再执着于表层化的生存的苦难,而是进一步指向了苦难之下的民族意识。
二 “文城补”之下的新秩序:川端康成式的哀伤和温情
《文城》的叙事在小说文本叙事时间的三分之二位置就结束了,之后进入《文城补》。《文城补》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按常规意味着三分之一的叙事时间很有可能都是“题外话”。本以为是余华在模仿莫言的《丰乳肥臀》,在正文结束后来几章长长的补记,补充一下情节的空白。由于莫言的创作一直极其稳定,所以《丰乳肥臀》的补记在叙事手法上与正文相比并没有什么显著差别,未造成震撼性的叙事效果。但余华就不同了,余华由写作后现代小说起家,横跨纯文学和俗文学两界,很善于制造高潮,手法经常令人匪夷所思,比如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及《活着》《兄弟》。《文城》更是如此。作为余华60岁时的耳顺之作,前半部分的“庄周梦蝶”叙事比较让人失望,一般读者可能都会“顺势”而想《文城补》又能补出什么呢?
谁曾想,一个从未有过的余华出现了。在“庄周梦蝶”叙事时段,余华似乎处于类似《现实一种》《死亡叙述》所代表的那种后现代暴力叙事时期的“混乱”状态,叙事漏洞比比皆是,几乎任何场景都让读者无法被代入。但进入《文城补》的叙事,一切都变了,叙述人似乎突然清醒了过来,像鲁迅重新从阿Q处抢过了话语权一样,低智的梦幻感完全消失了,叙事秩序重新建立,一切井井有条甚至大气磅礴。与前半部的混乱和各种叛逆式的“反叙事”手段相比,《文城补》像一个黑洞,吞没了所有的不和谐;同时,黑洞内部却是光明的,看似压抑的叙事之下涌动着某种深沉的令人感动的深情与真情。让人感觉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余华。
从叙事的功能和方法双向维度上来看,《文城补》无疑是从《文城》的“庄周梦蝶”演变为“蝶梦庄周”。此处,本文有意违反道家的无为式“无秩序”,把“庄周梦蝶”的道家公案儒家化或实体化(类似哲学化的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13]),“庄周梦蝶”意味着人类在现实世界想象另一个乌托邦世界,呈现的往往是天马行空般的梦幻之境;而“蝶梦庄周”则意味着于“多重生命宇宙”之下,反过来想象正常的人类世界,就像《山海经》《西游记》之类的中国神话和民间传说中有飞禽走兽山川草木等,返现就会指向一个正常的人类世界。所以与前半部相比,《文城补》竟突然展现出一个极其逼真的冷暖人间。于是《文城补》呈现出和前半部“庄周梦蝶”之时截然不同的叙事状态,比《活着》中的语言更加精炼、更有张力,某些段落甚至让人感觉仿佛看到了《红楼梦》的影子。
从修辞上看,《文城补》似乎通篇都弥漫着一种川端康成式的哀伤。川端康成式的哀伤为什么会在此时出现?或许是因为余华的创作生涯就是从川端康成开始的,“一九八二年在浙江宁波甬江江畔一座破旧公寓里,我最初读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他的《伊豆的舞女》。那次偶然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了写作”[14]。余华正是从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发现了那种哀伤式的美:他领悟到了文学“不是以一种控诉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在写”[15]。
《伊豆的舞女》发表于1926年,彼时川端康成27岁,处于中青年交界时期(相对于日本人1920年前后平均寿命约43岁[16],中国人平均寿命约37岁[17]),但小说所写到的实际经历发生在川端康成19岁时,所以更多呈现出一种青年的气息。要说更典型的川端康成的哀伤,当属1935年的《雪国》,当时川端康成36岁,加上时局的变化,《雪国》比《伊豆的舞女》的哀伤更显深重:
远山的天空还残留一抹淡淡的晚霞。隔窗眺望,远处的风物依旧轮廓分明,只是色调已经消失殆尽。车过之处,原是一带平淡无趣的寒山,越发显得平淡无趣了。正因为没有什么尚堪寓目的东西,不知怎的,茫然中反倒激起他感情的巨大波澜。[18]
现代小说一般以风景开始,以此宣示着发出者的“主体性”。而此处的风景最能代表主人公或叙述人的情绪,如柄谷行人所说“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19],正因为风景是发出者最佳的情感投射对象。《雪国》发表于1935年,川端康成时年36岁,按说应该是其作为男性精力最旺盛的年纪,但他却给人一种似乎过早进入中老年的感觉。其实考虑到当时日本人的43岁的平均年龄,说彼时的川端康成是中老年也不为过,何况其背后还有日本侵华战争造成日本“内卷”对其国人个体生命形成的巨大威胁。所以《雪国》一开始,川端康成就表现出一种优雅的、古典式的虚无。面对美丽的风景,却连用两个“平淡无趣”来表现风景“发现者”的无聊和空虚。自唐朝以来日本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宇宙观和生命观的很多方面与中国一脉相承,所以川端康成哀伤下的虚无不全是存在主义式的虚无,而是与中国道家和禅宗相通,是一种对生命体湮灭过程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无为”姿态。但人作为一个随时可能会逝去的生命个体,又不可能完全漠视生命,于是就和道禅的空无一起融合成一种生命既痛苦又不必痛苦、痛苦于既有意义又无意义的哀伤。所以,才有《雪国》开篇所呈现岛村那种奇怪的无意义感,与聚焦于其文字中到处可见的颓废以及存在意义上的游移不定。
川端康成《雪国》书影
在2021年的《文城》之前,余华其实从未明晰表达出类似川端康成式的哀伤。由于林祥福人物的低智式梦幻状态,这种哀伤感在上部几乎被摧毁殆尽。但到了上部的结尾,叙述人比谁都清楚另一个叙事空间就要开始,哀伤感一下子透纸而来:
道路旁曾经富裕的村庄,如今萧条凋敝,田野里没有劳作的人,远远看见的是一些老弱的身影,曾经是稻谷、棉花、油菜花茂盛生长的田地,如今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曾经是清澈见底的河水,如今混浊之后散发出阵阵腥臭。[20]
上述文本内容是《文城》上部结尾的风景描写。主人公已死,这个“认识性装置”所展现的“主体性”就完全是权威叙述人的,直接说是彼时彼刻的余华的心态情绪也没问题。美丽的乡村风景此时却“萧条凋敝”,田地“荒芜”,河水“腥臭”,只有“老弱的身影”。对于叙述人,“老弱的身影”暗含对于生命将逝的惋惜之情。短短几句风景,却时时处处散发着隐含作者发自内心的一种哀叹。
无论是川端康成的《雪国》还是《伊豆的舞女》,都以对美丽女性的描写来催化叙事。与之相似,《文城》一进入下部,小美突然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以主人公的身份正式出场。一出场她就貌似是婆婆眼中穷人家出生的漂亮且不祥的“妖孽”,婆婆要把她“教化”成符合传统礼教的媳妇。婆婆对她的摧毁正是从物质开始的,特别是那件让她眼睛“金子般闪光”的漂亮的蓝衣裳。这位死盯着小美的婆婆却又极精心理,连小美极为渴望能在没人时取出来穿穿那件花衣裳,她都坚决不允许,还上纲上线地将之认定为有不守妇道的嫌疑。十岁的小美就因为趁公婆不在家时偷穿蓝衣裳而第一次面临可怕的休书,婆婆居然能像宋明理学家一样神奇地从小美偷穿那件蓝衣裳,得出她犯了妇女的“淫”戒的结论。小美只能在恐惧中压抑地哭泣。
但是,这个“恶”婆婆身上却极深地隐藏着某种温情。实际上,无论是从其漂亮的外表还是战战兢兢的神态婆婆都非常满意小美。小美的漂亮外形和聪慧能干让她这个做婆婆的脸上有光,她在乡邻面前得意于自己有个漂亮悟性好手艺好且能干又听话的儿媳;而在自己威慑之下,小美像小鼠一样整天惊恐不安,一见她就浑身发抖口不能言,她极其满意小美这种畏惧她权威的状态,心知小美正是难得一遇的传统意义上的好儿媳的胚子。所以她直到临死前都喊着小美的名字,希望小美来接管家庭,她对倒插门的丈夫和无能的儿子不抱希望;此时,对于将死的婆婆,远去的小美何止是一个巨大的哀伤!只因为小美偷偷帮济了弟弟一点钱,小美在18岁时就已经被她一纸休书休回了家,人不人鬼不鬼地耻辱地活着。这个恶婆婆直到痛苦地离世都没再看到小美。而小美更为不堪的命运的转捩点在于,在母亲眼中原本不争气的儿子阿强违背母意带着小美私奔,其实是将小美带进了更悲惨的境地。阿强的无能让两人很快没钱山穷水尽,于是阿强想靠将“妹妹”小美婚配给林祥福来找出路。小美偷了林家的金条,再去与阿强碰头,但小美后来又给林祥福生了孩子,这成了小美必死的根源。林祥福的勤苦能干、善于经营和善良包容,让小美感受到了不敢想及的温暖和深爱,两个男人和一个孩子的痛苦拉扯,她一个“前现代”的柔弱女性无以承受,只得以死来清洗自己深重的罪愆。
所以,小美的死和林祥福的死一样,几乎都是必然的。弗洛伊德后期思想的某些方面与中国的东方生命观有隐约的相合之处,如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死亡本能”[21],“一切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22]。他认为这是生物进化的必然结果,因没有生命能永生,一切细胞和更复杂的生命体在细胞重复分裂到一定次数之后都会走向终点,所以弗洛伊德说的自我本能(回归本源)就是死亡本能。它类似东方循环时观下的生命必然轮回,那是一种面对生命必逝的坦然心态,一如庄周的妻死而己歌,认为生命归于天地之巨室反而令生者心境坦然。再者,一般人类的死亡本能都受到生命本能(性本能/繁衍本能)的压制而减弱,但有时候生的本能失去这种力量,就会导致死亡本能提前结束生命,我们称为“自杀”。小美和林祥福的死都接近自杀。在小说文本叙事空间里,林祥福是死在上半部,实际上是在小美死后十七年才死去的。他故意死于土匪之手,可能就是感觉到了梦早已破灭,他的存在已毫无意义,何况他的生命已在女儿林百家身上得以延续,寻梦幻灭让他提前进入生命轮回,这既是对生命的不屈,又暗合了寻小美而去的意味。而小美在林祥福到达溪镇后不久就死去了,表面上看是死于雪天的极寒,但她是在为林祥福和女儿祈祷中死去的,她无法面对两个深爱的男人和受苦的女儿,只能以一死来了结此生。小美只要活着就处于无法解除的多重痛苦之中,且永远无法拆解。再者,小美和阿强一起祈愿时被冻死,在某种意义上是完成了“仁义”的闭环叙事,对林祥福的道德亏欠似乎就此得以化解。但是,正值好年华的小美的遽逝,带给读者的是悲剧性的阅读感受,一个不到20岁的近于完美的女性双手合十,任生命一丝一丝地消弥于冰雪之中,怎么看都蕴涵着一种史诗般的悲凉。
还有,上部那种“伤心蜂拥而来”式错位修辞,《文城补》中仍然存在:
然后小美恢复了她的常态,一如既往的平静,但林祥福手里拿着一文钱恳求哺乳中的女人的情景,女儿一家一户进出吃着百家奶的情景,已在她脑海里定居下来,她时刻都会想起来,因此心酸不已,苦痛的感觉在她这里细水长流般的不再停息。[23]
实际上,《文城补》中破坏语法规则的“陌生化”修辞不但一直存在,而且远比上部中出现得更为频繁。上述短短几行段落就出现两处,一处是“情景”在她脑海里“定居”,第二处是“苦痛”“细水长流般的不再停息”。此处修辞似乎和上部中的同样不合时宜:有自主性的人才可能“定居”,静态的非人的“情景”无法完成这个动作。“苦痛”用诗意的、中性的“细水长流”来错位修饰,更是降低了人物痛苦的程度,叙述人似乎又像个长不大的年轻人一样在幸灾乐祸。但是,叙事的整体感消除了这种阅读不适感(《活着》中此种修辞手法也不断出现),令读者可以心无旁骛地一路读下来,这些陌生化手法都毫无违和感,皆因叙事如行云流水般前行,读者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叙述人的情绪吸引,强大的共情感不但让读者注意不到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存在,甚至一些原本怪异的修辞也被吸纳为小说叙事和谐的组成部分,融为一种与生命相奏鸣的诗感。这或许就是叙事的力量。
所以说,余华在《文城补》中突然制造了一个好似可以超越一切的叙事黑洞,由“混乱叙事”突然转入“完美叙事”。在这个叙事黑洞中,读者的无法代入感也突然消失,故事一下子变得引人入胜,时时牵动着读者一些极细微的情思,并引发于细微情思之下潜藏着的巨大的感动,令人无法漠视小说叙事中所埋藏的那绵延不尽的温情。这时《文城》中美丽而温柔、坚忍而压抑的主人公小美,像沈从文《边城》的女主人公翠翠一样,牵动着万千读者的心。她或许比未经“教化”的翠翠更符合男权视角之下的东方女性想象,清秀、美好、温顺、乖巧、勤劳、忍耐、胆怯、沉默,每一个元素都能精准地击中读者心底的痛。小美又是一个封建男权社会的被压迫妇女,她在努力地争取活着的权利。婆婆作为男权之奴,时时带给她生命的威压。婆婆偶有的温情都让她感动,但终于还是一纸休书彻底摧毁了她的人生。她一直摆脱不了婆婆、世界的控制和压迫,直至香消玉殒在极寒雪天之中。生命终结的瞬间,她心中留驻的是爱与温情。她的自我救赎式的自我毁灭,与林祥福一生的追寻或苦难,构成双重的人生悲剧。其实,有找寻目标的人还是幸福的,追寻其实带来一种蕴涵温情的希望。小说中,林祥福在去与土匪谈判前就已经抱了必死之心。送赎金为什么就要死?难道是余华的又一个叙事漏洞?其实,余华这样的叙事安排,正是应对后半部的倒叙中,彼时小美业已死去、而一直追寻小美的林祥福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从而完成了既具逻辑合理性又令人心痛不已的完整的闭环叙事。
三 哀伤和温情之下强大生命力的展示
如果只有川端康成式的哀伤,余华最多就是第二个川端康成。但余华超越了川端康成,就成为了中国唯一的余华。秉承中国五千年文明,余华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群体意识融入了小说,形成儒道传统下的“天人合一”的个体命运与群体存在较完美融合的理念。而川端康成更多地表现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和控制下的个体意识,中国文化仅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影响了他,故川端康成的哀伤是指向个体的,缺乏群体感。川端康成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下对群体的存在和力量基本上是无动于衷的,而余华却时时感受到群体的悲欢离合,这是对群体生命力的展示、亦是其心怀民族国家历史的表现。余华《文城补》写出了底层人民的悲壮史诗。不是像《活着》一样渲染各种压迫下弱者的不断死亡,而是更进一步,从生命角度强调弱者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和内部压迫下的顽强生存,哪怕毁灭也体现顽强的生命意志力。它指向一种深刻的文化和精神拷问,一种深藏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强大生机。
《文城补》的“蝶梦庄周”叙事开始于小美的“蝶变”期待。作为贫穷人家的女儿,十年的食不果腹和衣衫褴褛让她非常急于摆脱贫穷的身份,发生自己人生的“蝶变”。叙述人特别强调她走在镇上,各种琳琅满目的衣物饰品食物让她眼中一直闪着“金子般明亮的颜色”[24]。叙述人会通过叙事频率来有意加强某个行为或意象,叙事频率表现为叙事的重复[25]。“金子般明亮的颜色”在《文城补》第1节的3页零3行的叙事时间内出现了4次,这种“重复N次发生N次的同类事件”的重复手法,正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同类行为的重复,强调了小美极其渴望和向往幸福生活,具备她想“蝶变人”的强烈意愿。从消费主义来看,“金子般明亮的颜色”不过是人的“物化”和被资本意识形态控制的标志,类似德莱赛的《嘉丽妹妹》中女主角对芝加哥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的极度向往;但是,对于挣扎于生存和死亡之间的中国乡村底层平民,一个极柔弱的乡村女孩子,向往更好的物质生活本是一种美好的人生期待,一种生存的强大动力,本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品质,在困苦中能吃苦并永远对美好生活保持向往与追求的动力,这也对应着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源头——从“本质”上看,小美的这种期待和自古以来文人“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的“理想”殊途同归。出身极苦,但美丽的外表和伶俐的手脚给了她一个“蝶变”的机会,她和一个小商人家庭的儿子订了亲。但令她想不到的是,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给她带来巨大的伤害,直至毁灭。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6],余华就是通过小美这个弱者的毁灭,建构出了史诗化的哀伤感。看似个人的悲剧,实际上小美代表的是旧时代的一个群体,余华对她是倾注了理解与惋惜的,那是一种生命力被封建传统摧残的人类悲歌。
《文城补》写出了弱者生命存在呈具的巨大哀伤感,以及哀伤之下笼罩一切的悲悯,那是儒家式的对于天地生命的同情。余华《文城补》所呈现的小美原生家庭极度贫困的状况,令人震惊却又合情合理,刻画得极为精妙。在婆婆家做童养媳6年之后,16岁的小美面临“圆房”。婆婆为了省钱,只举行了简单的拜堂仪式,请小美的父母来吃顿饭草草了事。富亲家相邀,小美的父母喜不自胜,同时带来了小美的三个兄弟,这让婆婆很是意外。五个乡下人在婆婆家无时无刻不暴露着贫穷之下的极度自卑感。余华是独具叙事天赋的小说家,他对五人的双手和袖管之间的关系作了绝妙的描述:
婆婆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这五个来自万亩荡的贫穷亲人却是胆怯地吃着。虽然他们饥肠辘辘,虽然桌上的鸡鸭鱼肉香气扑鼻,可是他们的双手仍然插在袖管里,仿佛是在互相等待,当父亲的手从袖管里出来,拿起筷子夹一块肉放进嘴里后,另外四个的手也从袖管里出来,也拿起筷子夹肉。父亲的双手重新插回袖管后,另外四个的手也都跟着插回袖管。然后又是等待,下一个是小美的哥哥,他勇敢地将手伸出袖管,另外四个受此鼓舞也伸出袖管里的手,当小美哥哥的双手回到袖管后,其他人的手也都回归袖管。就这样,他门的手从袖管里迅速出来,又迅速回去,快去快回像是小偷的手。[27]
“袖管”在短短半页纸里出现了10次,通过双手进出袖管的细节,表现了食不果腹的穷人在突然面对一大桌大鱼大肉之时,心中一片狂喜却又强忍口水,碍于颜面要寻找一个从容又“知礼”的“出筷”方式。于是“袖管”成了一个道具,手在袖管里,就是安全,就是知礼,就是自尊;手出袖管,就如出鞘之剑,顶着羞耻和失礼的压力,“他们的手从袖管里迅速出来,又迅速回去,快去快回,像是小偷的手”。看到此处,一般读者都会觉得非常好笑。其实,这是极有意味的细节描写,尽显穷人的辛酸,让人感觉《活着》的极限叙事又出现了。同时,这种“重复N次发生N次的同类事件”的重复手法的再次使用,无限加强着弱势群体存在的羞耻感和悲剧感,似乎又重现了《许三观卖血记》中的叙事神韵。这是更深沉的含泪的婉讽与悲悯,底层小人物的困窘和贫穷所带来的耻辱感被表现得入木三分,婉讽之下是远比《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更为深沉的悲悯。须知《活着》执着于“苦难”,将生命力埋没于刻意安排的家人的全部死亡,《许三观卖血记》实际比《活着》更忽视了底层生命的光明面、而有些流连于猥琐维度的日常化的存在。
《文城》却处处埋下光明的“辩证法”,小说中不断强调小美和林祥福的勤劳与劳动能力的强大及对“幸福”的渴望,使人时时想到“袖管”的耻辱感和阿Q式的“好面子”之下正是一种普遍化的民族性的蓬勃生命力,可以说它是中国崛起的民族精神源头之一——“知耻而后勇”。与隐含作者让恶婆婆在虐待小美的行为之下还深深地隐藏着某种温情一样,婆婆临死前对小美的呼唤是因潜在的良知未泯和祈盼家族血脉还能得以延续。于此,叙述人非常包容且悲悯地昭示了悲壮的生存伦理,以及善恶相依的人间“相对真理”,即婆婆对小美所施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实际上暗含着中国民众的一种坚韧的生存观:不管生活多苦规矩多么苛严,都是为了让子嗣被教养成可以传承下去的个体。而施虐者本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言行的无理与不合理之处,她只是想规矩出一个好儿媳,所以对于婆婆与小美而言,其实是双重的悲剧。前现代人民全力应对人世多舛之下依然潜藏一种“残酷”的温情。
哀伤和温情结合,造就了《文城补》巨大的叙事感染力;而与隐藏的生命力互相辉映,形成了《文城补》强大的精神力量。于是,《文城补》所展开的恢宏叙事就凝成了一个无比深沉的生命洪流。《文城补》中有关小美的“蝶化庄周”叙事为余华铸就了一个成功的重大转折。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城》上部的“混乱”恰恰为下部关乎小美叙事的叙事魅力积累了无限的“势”,使小美所具有的超乎寻常的诱惑力、生命力与象征意味都变得可解了。主人公小美一出现,就立刻成为一个核心叙事元素。可以说,《文城补》才是小说的主要部分,篇幅长出一倍的“《文城》”就像铺垫、是长长的“序章”。从小说中看,文城之名来自一个谎言。阿强对林祥福随意编造了一个叫“文城”的地名,事后小美曾经问阿强“文城在哪里”,阿强回答说:“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28]。文城是一个虚构之地,是给林祥福设的骗局,也是隐含作者给读者设的骗局;但林祥福不知情,反而为了小美拼力去寻找它,它在林祥福心里是一个梦想之地。对于林祥福而言,“文城”宛如一个图腾般的存在。在《文城补》中,文城虽然不显,但又似处处是文城,小美所在即文城。文城和小美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共同建构了一个充满希望、绝望与追寻的人类传奇故事。林祥福和小美的生与死之下都潜藏着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正是他们共同铸就了《文城补》中那动人心魄的叙事魅力。
可以说,余华《文城》的成功是一个儒家“内圣外王”[29]式的成功。第一是“内圣”,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修为,把文学水平提升到尽可能高的高度;第二是“外王”,为文坛的整体进步乃至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影响而写作。两者余华都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余华的儒家式努力还有一个更重要更有价值的表现,就是努力地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动力乃至文化根源,特别是苦难与死亡之下的生命力。余华把小美作为一个旧时代被压迫妇女的美与挣扎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并通过林祥福等人物指向更深刻的民族生存问题。作为具有象征意味的人物,林祥福在哪里都有着卓越的吃苦耐劳和发家致富的才能,小美体现着中国女性贤淑勤劳的优秀品质,在哪里都能井井有条地管理好家庭。所以,林祥福和小美对梦的执着和深切的痛感,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优良传统的表现。这些都很完美地结合于《文城》之中。这也是余华第一次表现出一种堪称大师级的叙事风范。
在儒家之外,道家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诗品》《文心雕龙》到《沧浪诗话》,无不强调超功利的文学观和文学的空灵情境,即道禅的无我化境。它与儒家的言志结合,在世俗生活中就凝聚而成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的终极之源——进可内圣外王,退可清净无为,有志者皆可努力实现自己的家国理想,一如苏东坡进退无忌,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儒道互补,都能够将个体、人民和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在“文城”之外,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在写作上不断创新不断提高的余华。余华在2021年的《文城》中,既完成了对自己创作的超越,又形成了他文学创作迄今为止的第四次叙事转折;而对于当代文学本身而言,余华的《文城》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与意义。余华有望跻身世界一流文学大师的行列,因为西方很少有作家能够建构出如《文城》这样简单凝练却蕴藏着深深的人类之痛、人性之美和民族生命力的叙事。
或可以说,《文城》让余华走向了一个新高度,也给其他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走向世界的小说样本。在未来岁月里,诺贝尔奖的所有奖项,将有更多的中国人的身影,这无疑都会是越来越有力的中国力量的证明,诺贝尔文学奖自然离余华也会更近。诺贝尔奖终将不再是或不应再是中国作家的一个“焦虑”,未来它将仅仅是作为一个佐证而存在。
注释
∨
[1] “理想读者”“预期接受者”皆指作者写作时预设的读者,是完全理解作品的理想化接受群体。参见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第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周伟达:《〈文城〉之前》,《新民晚报》2022年5月29日,第7版(夜光杯)。
[3] 这是《兄弟》出版后评论家在表达对余华的失望时的自称,“一边是《兄弟》(上)的热销,另一边是专业读者的集体沉默”。见张英、宋涵《余华现在说》,《南方周末》2006年4月27日,文化版D25。
[4][7][20][23][24][27][28] 余华:《文城》,第160页,第5页,236页,第334页,241页,第252页,第330页,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出版社2021年版。
[5]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第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6]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8][25]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第54页,第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9] 普罗普:《故事形态学》,黄放译,第18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10] 托多罗夫:《散文诗学》,侯应花译,第5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1] “行动元”指功能性的人物角色,格雷马斯把普罗普的“角色功能”归纳为六个“行动元”以及由此两两结合而成的三组施动者范畴,即主体/客体、发出者/接收者、辅助者/反对者。参见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蒋梓骅译,第257—26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2]刘旭2018年在《余华论》中总结了余华创作的三次大转折:后现代转折(《十八岁出门远行》)、温情转折(《活着》)、消费主义转折(《兄弟》)。
[13] 《黑客帝国》(Matrix)三部曲,沃卓斯基兄弟导演,里维斯主演,1999—2003年上映,为百年来哲学化程度最高的好莱坞电影之一,预设了1999年的人类世界实际是电脑给人类制造的虚拟世界,正像庄子活在蝴蝶的梦里。
[14] 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参见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第91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15] 余华:《我的文学道路》,参见余华《说话》,第7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6] 参见《朝日新闻》社稿,《“长寿国日本”长寿——何时是尽期?》,张景柏译,《人口学刊》1984年第1期。
[17] 赵锦辉:《1949年前近40年中国人口死亡水平和原因分析》,《人口研究》1994年第6期。
[18] 川端康成:《雪国》,高慧勤译,第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第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1][22]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弗洛伊德文集》(四),杨韶刚译,第28页,第29页,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
[26]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1),第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9]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核心规则,最早出自《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见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69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关键词: